第三届中国民族音乐传承周丨周娟:坡芽歌书,织就人类共通的深情几时




在云南的文化长卷中,坡芽歌书是枚独特的印记——81个用仙人掌汁写下的符号,对应一首首婉转的民歌,藏着壮族先民的爱情絮语与人生哲思。
当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周娟接到为云南坡芽歌书合唱团、中央音乐学院艺境民族室内乐团创作融合作品的任务时,一场与云南的音乐对话便已启程,最终凝结成一曲《几时》,让时光里的爱与深情,都落在了旋律上。
周娟与坡芽歌书的初见,是一场“慢慢来”的打动。早闻这是国家级非遗的“爱情密码”,但当她真正伏在案前,对照汉译歌词逐首梳理81首民歌时,才真正触到这份文化的温度。
“将爱情观与人生观融为一体,从‘小伢伢’一直唱到‘伫立幕墓前’,这不仅是壮族人民的爱情故事,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爱情观和人生观。我就想把这个结构体现出来,唱出爱在时空中延伸出的不同层次和意义。”谈及创作灵感,周娟深觉坡芽歌书的美,不仅是单旋律的清甜,歌词里也满是家常的具象比兴。
“爱不是单薄的你侬我侬,那太脆弱;它是永恒的力量,它可以是‘心乱似沸油’,也可以是‘花开在房中’,失去时‘肚肠拧成绳’,渴望时‘变作路边树’,它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,也是我创作《几时》的出发点。”
在周娟看来,壮族人的爱情观竟与全人类的情感底色无缝契合,这份对“爱”的通透理解,成了《几时》最初的创作原点。她像个时光的拾贝人,从81首歌里拣选29句歌词重新排序,让旋律跟着情感走,也跟着壮族先民的生命轨迹走。
这场创作从一开始就带着“冒险感”——为云南26个壮族人声与北京9件八音代表性乐器谱曲,这样的编制此前从未有过,两个乐团也未曾有过合作经历。
“两地排练时,大家都在心里猜:对方的声音会是什么模样?”周娟笑着回忆起首次合成排练的场景:艺境民族室内乐团的成员风尘仆仆赶到云南,饿着肚子放下行李就奔上台,胡瑜教授的指挥棒一扬,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音乐团体,第一次在旋律里“认亲”。
当最后一个音符的余韵消散在空气中,没有多余的寒暄,音乐家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。“大家终于在音乐中相遇、相知并惺惺相惜。”周娟说,这场跨越千里的声音碰撞,没有惊天动地的“乐器灵感插曲”,却有着最朴素的感动——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体系,在《几时》里找到了最舒服的相处方式,就像云南的山与北京的风,相遇时自有默契。
“坡芽歌书的音乐软糯,歌词更是古风而雅致,汉译后的五言句式就像《诗经》里那样读来满口余香。”在周娟的印象里,云南民族音乐多是载歌载舞的热烈,壮族音乐却有着独一份的温和与内在力量。
于是,她在脑海里构建了一幅画面:一个人伫立在爱人墓前,身后是云南连绵的群山。旋律从悲痛欲绝的器乐引入,跟着他的视角倒回时光:先是“独自上山冈、风来独忘家”的儿时嬉闹,再是“外边谁唱歌、唱得妹心跳”的青春悸动,接着是“锡银汁共熔、花开在房中”的幸福相守,又滑向“星移两分离”的离别之痛,最后落于“变作一棵树,每天见几回”的绵长念想。
“我用国际化的合唱手法丰富原民歌的单旋律,再配上细腻的民族室内乐,就是想让歌书里的唯美与悲伤,能真正‘立’起来。”周娟说,她不想把壮族音乐框在“地域标签”里,而是想让这份细腻,触到每个人心里最软的地方——毕竟,关于爱与离别,本就没有民族之分。除此之外,周娟让坡芽歌书传承人将两首原生态民歌对位在作品中,在丰富的和声设计之上,充分尊重他们的原曲原调,从音响上赋予民歌更深厚的情感含义。
《几时》的诞生,藏着无数个“纠结的日夜”。
“从接到命题开始,天天都在卡壳。”周娟坦言,要兼顾坡芽歌书的原味、民族室内乐的特质,还要用国际化技法来结构,让她常常陷入“早上写了晚上删,晚上写了第二天早上改”的循环。好在学院与云南方面给了她最大的创作自由,让她能彻底“泡”在坡芽歌书里,反复琢磨“守正创新”的真谛。
“既延伸坡芽歌书新时代的生命力,也吸纳壮族音乐文化为民族室内乐带来多元语汇,并使用国际化的创作技法将这两种编制有机统一。”周娟说,所谓“守正”,是守住坡芽歌书里的情感内核;所谓“创新”,是用新的音乐语言,让这份情感被更多人听见,《几时》不是把民族元素和现代曲风硬拼在一起,而是让它们互相成全。
当她把最后一句“几时?”的旋律定下来时,突然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——像是坡芽歌书本身,在引导她写出它该有的样子,当合唱团员们唱到眼泪汪汪,她忽然觉得此心归处,便是吾乡——“他们被属于自己民族的词谱成的新音乐打动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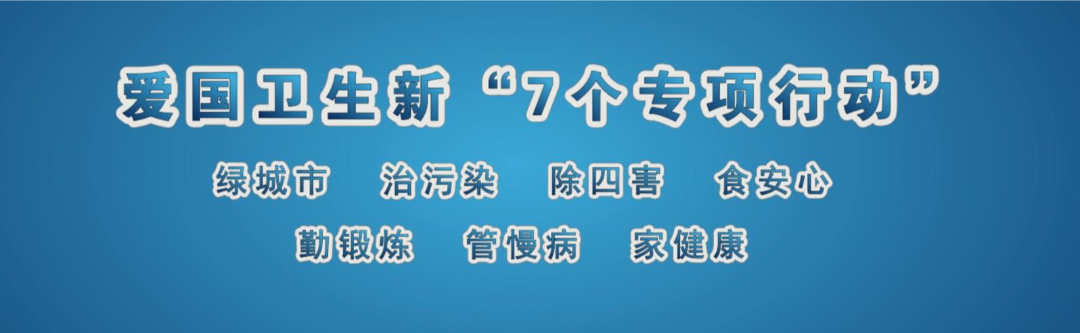
来源:
编辑:廖珊珊
责编:王开敏
审核:董高杰
新闻热线:0876——7133230
